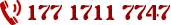学术研究
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问题研究【连载三】
作者:李耀辉 导师:周宝峰
【作者基本信息】 内蒙古大学, 法律, 2012, 硕士
二、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比较考察
(一)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
1.英国
英国1679的《人身保护法》首先肯定了被告人的辩护权,该法明确规定了诉讼中的辩论原则,承认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从而确定了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
根据英国法律,嫌疑人在侦查的任何阶段都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即使他受到了羁押。但前提条件是,不会因此导致不合理地拖延或妨碍侦查程序或审判的进行。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主要辩护活动是:一、与嫌疑人进行通讯联系;二、在警察询问开始之前会见嫌疑人;三、在警察讯问嫌疑人时到场。当然,律师进行这些活动的前提是不会妨碍侦查程序或审判,否则即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
在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the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1984)首次明确地赋予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侦查阶段的获取法律咨询的法定权利。[1]该法的《实施细则C》(Code C of the Codes of Practice)规定,所有被警方拘捕的人都必须被告知有权随时以书面、书信或电话的方式与独立的律师取得联系,并且可以获得值班律师免费法律咨询;任何警察不得在任何时候以任何语言或行为阻止被拘捕人取得法律帮助;原则上只有在被拘捕人实际取得法律帮助之后才能对他进行讯问或者继续讯问。如果询问开始或进行过程中被拘留者被允许咨询且有可能咨询到律师,则必须允许该律师在询问过程中在场。但英国辩护律师讯问在场权缺乏必要的保障,没有美国的“如果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没有律师在场,则讯问无效”的规定。
在英国,获得律师有效辩护已经被判例法确认为刑事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国际人权公约也在许多地方规定辩护律师应向其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协助”,有效辩护由此在法律上演化为辩护权的权利要素之一。相应的,“对获得有效辩护的保障不可避免地产生这一权利受到侵害时如何救济的问题”,于是,便合乎逻辑地产生了用于解决此类问题的无效辩护制度。英国的无效辩护制度是保障刑事被追诉人获得律师有效辩护和公平审判。英国历史上并没有形成如美国一样的成文宪法或宪法性权利法案,因此,英国的无效辩护不是产生于对被告人宪法权利的解释,而是起源于判例法。早在设立刑事上诉法院时,当时的总检察长就指出,辩护律师的误算和失职将会构成一个有效的上诉理由,“如果被告人律师的辩护行为是失职的,辩护律师没有提出其应该提出的问题,并且对应该举出的证据没有举出, 所有的这些问题将能够导致上诉法庭对该案件进行审查,并且对有罪判决是否成立作出判决”。[2]后来产生了一系列与无效辩护有关的判例。英国上诉法院于1988年在R.V.Ensor案[3]中第一次对律师辩护的质量标准问题作出了回答。在此案中,法院认为,如果律师所做的令人不能容忍的、过度失当的辩护使被告人蒙受不公正判决的危险,同时判决结果存在着非正义的潜在的疑问,上诉法院可以撤销第一审法院的有罪判决。据此,律师的辩护行为是否有效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律师辩护行为本身是否“过度失当”以致“令人不能容忍”;二是律师的辩护行为致使判决结果存在着不公正的可能性。随后,皇家刑事司法委员会认为R.V.Ensor案所确立的无效辩护标准过高,在其报告影响下,上诉法院于1993年在R.V.Clonton[4]案中放宽了无效辩护的标准。高判决指出,以是否具有重大违法性来判断律师过失,这容易造成陪审员认识上的混乱,是不妥当的。而且,并不是所有出于善意的辩护行为都不存在问题,例如律师所做的决定超越了作为辩护人应当遵守的合理建议的范围内;律师对被委托的事项无所作为等,根据《形事上诉法》第2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可以撤销陪审团的决定。判决认为,以辩护质量来衡量律师行为的正当性过于看重形式无助于解决问题。只有审查律师的不当行为对审理和裁决造成的实际影响才具有现实意义。据此,R.V.Clonton案确认的无效辩护的标准更看重的是辩护律师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而不再集中关注辩护律师的错误的种类。在英国,被告人提出无效辩护申请的理由通常包括被告人在司法过程中没有从辩护律师处获得充分的保护,律师对诉讼的准备不充分,律师没有给予被告人适当的法律意见,律师在审判中没有传唤证人出庭作证,律师的能力缺陷,等等。[5]
在英国,法律援助作为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英国法律援助的模式被称为“朱迪凯尔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就是由开业私人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民事、刑事法律服务,费用由政府支付。该模式起源于慈善团体、社会组织对穷人提供的司法救济。相对于专职律师而言,它能提供更为方便、专业的法律服务,受到英国民众的普遍赞誉。[6]英格兰于1966年设立了刑事诉讼法律援助部门—维奇瑞委员会(WidgeryColnlnittee)。该委员会在除了肯定既有的由私人执业的律师单独提供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费用由国家按案件支付的做法外,还建议在法律援助案件中实行当事人挑选代理律师的做法。该委员会还认为,赋予法律援助应当成为上级刑事法院收审案件的准则,一方面,建议对治安法院授予法律援助更严格的标准,只有在下列情形下才可赋予法律援助:如果被告人被判有罪就会失去工作、名誉或面临监禁的真实危险,或者当辩护包括实质性法律问题或需要追查和询问证人,或者由于代理被告人就必须对控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或者为了被告人以外的其他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维奇瑞委员会建议,当被告人做有罪答辩时,一般不要求给予律师代理和法律援助。这些标准被称作“维奇瑞表标准”,现在这些规定都写入了《1999年司法准入则》(the Aceeess to Justice Act 1999)第三部分中。[7]为保证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法律服务委员会设计了一套专家质量评分标准,用于评价不同种类的工作,提供者要想成为签约事务所,必须获得一定的质量分数。而对于疑难复杂案件,则采取了一些特别的措施保证质量,比如采用大案管理体系,与律师事务所单独签订合同,或建立专业名册制度,要求具有一定专业水平和办案经验的律师才能参与办案
英国自从实施了警察和刑事证据法后建立了所谓的“值班律师计划”,只要被逮捕者不放弃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政府将及时为几乎所有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一般而言,警察局必须在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24小时内为其提供一名事务律师,并安排他们会见或者联络。即使在特殊情况下,这一时间也不得超过36小时。如果事务律师想要成为一名值班律师,必须经过听取周围人的评议而举行的地方选拔程序,并且只有同一律师事务所内的其他律师可以代替其在警察署内提供法律服务。英国律师协会曾颁布一项指南,要求在警察署内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都应当精通刑事法律,这表明英国已经在贯彻律师的有效法律帮助原则。
2.美国
(1)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权的发展历程
美国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在一切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享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尽管第六修正案明确表述刑事被告人应当享有获得律师帮助权,律师在抗辩制中处于核心角色,但是对于聘请律师的权利,是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说明其法律含义的。
在1932年,最高法院通过Powell诉Alabama[8]一案的裁定,认为在死刑案件中,法院应当为无人辩护的被告人指定律师,否则就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所规定的正当程序原则。此案中,最高法院依据的不是第六修正案对聘请律师权的保证,而是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它隐含了一个原则即刑事被告人应当获得公正审判。而且该裁定的适用范围也是非常有限的,即在死刑案件中,如果被告人不能聘请律师并且不能为自己辩护的话,法院必须为被告人指定律师。在1938年的Johnson诉Zerbst[9]一案由布莱克大法官起草的意见中,法庭认定,在联邦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犯重罪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如果被告人无力支付聘请律师的费用,法庭有义务为其聘请律师。与Powell案不同的是,Johnson案依据的是第六修正案对获得律师帮助权的保证。在Johnson案之后的25年间,最高法院拒绝将这一裁决扩展适用到州法院审理的案件当中。各州审理的案件仍然适用的是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最高法院在1942年的Betts诉Brady[10]一案的判决中认为正当程序原则只有在某一特定案件的特殊情况(特殊情况标准)表明这一贫穷被告人只有通过律师帮助才能获得公正审判的时候才要求提供指定律师。并且法院确认其在Powell案中的观点,也即在州刑事诉讼中获得律师帮助权是依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此案的判决阻碍了第六修正案对获得律师帮助权的发展,但是最高法院仍继续依据Betts案的“公正审判”规则,来审查在没有律师帮助下作出的判决。1963年的Gideon诉Wainwright[11]案,认为刑事案件的辩护人系必需品而非奢侈品,当被告人所犯为得科处自由刑之罪时,即应为其指定辩护人。在该案中,最高法院首次认定第六修正案律师权条款适用于各州,并放弃了Betts一案中适用的特殊情况标准,将在州法院审理的案件当中所要求的获得指定律师帮助的权利扩展到所有贫困的重罪被告人。同年,在Douglas诉California案[12]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由州法律所赋予的在第一次上诉时贫困被告人获得指定律师帮助的权利是一种平等保护上的权利,所以被告人在第一次上诉中,法院必须为贫穷的原审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1966年的Miranda诉Arizona[13]案,认为在被告人受拘禁或自由受限制之情况下,实施讯问前应先告知被告人所具备之权利,尤其是委任律师之权利,并且在审讯的时候有律师在场,如果该人是贫困的话,将会为其指定一名律师进行代理。米兰达一案中的做法,即认为赋予嫌疑人和律师咨询的机会是保证实现其他的宪法性保障的一种方式。1967年,在Mempa诉Rhay[14]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只有在一些关键阶段,也即那些缺少律师帮助将会影响到被告人实体权利的阶段,被告人才享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同年的美国诉Wade案,认为辨识犯罪人而进行列队辨认( line-up)之过程中,应有辩护人在场协助。在1972年,Argersinger诉Hamlin[15]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无论被告人所犯为重罪、轻罪抑或微罪,只要有科处自由刑的可能,即应有律师的帮助。在1975年的Faretta诉California[16]案中,最高法院确立了自力诉讼的宪法权利,并指出,自力诉讼的被告人必须以其有意识的、明智的方式放弃那些与律师帮助相联系的传统利益,选择自力诉讼的被告人不能因此抱怨其自我辩护的实质等同于剥夺了其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权利。斯图尔特大法官在Faretta一案中指出,“如果,并且仅当被告人要求帮助的时候,州可以——甚至可以忽略被告人的反对——指派一名‘备用律师’帮助被告人,并在有必要终止被告人自我辩护时作为被告人的代理人。”1979年的Scott诉Illinois[17]案,联邦最高法院认为,除非各州已为其指定了辩护律师,否则任何一个穷困的被告人都不能被判处监禁以上的刑罚,也就是说没有必要为判处监禁以下刑罚的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在1984年的United States诉Cronic[18]一案的判决意见指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权利实际上就是被告人的一种要求控方提供的案件事实能够经得起真正的对抗式的标准检验的权利。在1984年的Strickland诉Washington[19]案,联邦最高法院首次涉及律师帮助的效力问题,并以反列举的方式界定了判断律师帮助的效果的标准,并认为此标准对聘用律师及指定律师均有约束力。在1985年的Evitts诉Lucey[20]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如辩护人不能提供有效的律师协助,与无辩护人无异。”在Smith诉Murray[21]一案中,最高法院后来将“Strickland案的标准”适用到了所谓的上诉律师不称职的问题上。Hill诉Lockhart[22]一案同样判决认为Strickland一案的由两部分组成的标准适用于基本所谓的律师帮助无效而对有罪答辩所提出的质疑。在1986年的Nix诉Whiteside案[23]和Murray诉Carrier案,作出了对Strickland标准的补充,分别指出:在被告人意图作伪证时,辩护律师的劝阻行为不构成无效帮助;当出现程序错误时,如果该错误是因为律师的辩护策略而导致的,则该程序错误不构成无效帮助;而只有当该程序错误是出于辩护律师的疏忽大意并导致对被告人的不公正判决时,该程序错误才构成无效帮助。在1993年的Lockhart诉Fretwell一案中,最高法院确实指出,“‘Strickland标准’的不公正成分关注的是律师的不尽职行为是否使审判变得不可信赖,或者使程序从根本上是不公正的”,而不能仅仅因为在有关审判结果的问题上合理可能性标准被满足就一定会导致以上情况的出现。不过,该案的裁决并没有使其论述超过这样一个原则,即“如果律师的无效帮助并没有导致被告人被法律所授予的实体性和程序性的权利受到剥夺的话,就不会产生不可信赖和不公正的情况”。
(2)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权的宪法标准的演进
联邦最高法院在Strickland诉Washington案中认为:“获得律师的权利就是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权利”。所谓的律师有效帮助,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判断律师的帮助是否“有效”。就此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争辩与演进,并在1984年产生比较明确统一的见解。
美国最高法院最早在Powell诉Alabama案中承认被告人有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宪法性权利。10年以后,在Glasser诉UnitedStates[24]一案中,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在一个联邦案件中,如果某一司法行为否认被告人有权获得律师的有效帮助的话,则该行为已经违背了第六修正案的有关规定。在承认第一次上诉中被告人有平等的权利来得到指定的律师之后,最高法院认为提起这种上诉的被告人也拥有获得其上诉律师有效帮助的宪法性权利。在1970年以前,大部分法院对于律师有效帮助的判断标准是“荒诞剧和笑柄”的标准。根据Gideon案判决时的法律,法院认为,律师应提供有效的帮助,他们在法庭上代理行为不应是“荒诞剧和笑柄”式的代理。这一标准来自Betts诉Brady一案确定的公正审判的诉讼程序。在此标准下,被告主张未受到律师的有效帮助,必须证明审判是一场闹剧,极为困难。Gideon案后,许多人希望法院能够根据一个更高的标准来衡量律师的辩护行为,以提高辩护的质量。
在为改变律师代理标准的争论中,当事人及评论家们认为被告人应当有权得到一个合理、有能力的律师代理,而不仅仅有权聘请律师,法官们则不同程度地抵制了这些主张,法院不愿改变这一标准是基于对改革后果的忧虑。法院的这种担心主要理由有三:(1)如果律师的行为稍有瑕疵,上级审法院就必须撤销原审判决,将会破坏判决终局性,再者会造成法官过渡干涉辩护行为,法院只要怀疑律师的行为可能有瑕疵,即必须随时介入。(2)如果法院过于严格检验律师的代理行为,会导致律师不愿意接受法院指定的案件。(3)对于胜诉机会不大的案件,律师可能会故意犯错制造瑕疵,成为上诉翻案的原因。
克服了这种担心之后,法院最终开始倾向那些主张抛弃“荒诞剧和笑柄”标准的意见。在1970年的McMann诉Richardson案,提出所谓的“合理胜任”标准。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只要律师所提供的建议,是刑事辩护律师所认可的适当范围内,即为提供律师的有效帮助。
对于“合理胜任”标准,许多法官和学者批评其模糊不明确。联邦法官Bazelon又提出“逐项检查或类别化”标准,即先将律师应有的辩护行为予以逐项明示或类别化,并检视律师在个案中是否逐项做到应有的辩护行为,藉此设立辩护人最起码应达到的最低标准,如未达到应有的最低标准,即视为未提供律师的有效帮助。此标准重视辩护人的行为表现,至于辩护行为是否会影响判决结果,在所不问。此标准获得众多学者的支持,但并未被大多数法院所接受。
在1984年的United States诉Cronic案[25]中的下级法院以行为本质来判断方法进行了引申,从而认为律师必然不能提供有效的帮助,即推论律师不能基于以下五种因素有关的情况而免除其责任:(1)可以用于调查和准备的时间;(2)律师的经验;(3)指控的严重程度;(4)可能的辩护理由的复杂程度;以及(5)律师接触到证人的可能性。史蒂文斯大法官在判决意见中认为,下级法院所采用的这种“推论方法”缺乏最高院过去的先例支持,并且与有效帮助要求的功能不一致。由此得知,律师帮助的无效性不能根据辩护律师以上标准进行推断。然而,在过去最高法院的判决中,史蒂文斯大法官发现在两种情况下这种推定的方法是才具有正当性:第一种情形是,“在诉讼的关键阶段,律师或者根本没有出庭,或者被阻止为被告人提供帮助”。第二种情形是,在某些的情况下“被告人在审判期间虽然可以得到律师的帮助,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律师,甚至是一个相当优秀的律师,如果他能够提供有效帮助的可能是如此之小的话,即使在没有调查审判的实际活动时,也可以推定这是不公正的。”
1984年的Strickland诉Washington案[26],联邦最高法院终于确立此问题的宪法标准。Strickland诉Washington案表明,如果辩护律师有以下行为,其为被告人提供的帮助是无效的:(1)律师有瑕疵行为,没能有效的发挥作用;(2)律师所犯的严重错误对被告人造成了不利影响,且导致被告人无法获得公正的审判。1984年之后联邦最高法院还指出被告人未受律师的有效帮助有三种情形:(1)辩护人造成的错误。例如辩护人对重大法律不了解,影响被告权利的实现,就不是有效的律师帮助。(2)政府的干涉行为。例如在审判中休庭等待翌日继续开庭,禁止被告与律师会谈等,即为非法干涉辩护人的辩护行为。(3)利益冲突。例如辩护人同时为利害相反之二共同被告辩护,也不是有效的律师帮助。
在1993年的Lockhart诉Fretwell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制定了更难以推翻定罪的标准,即根据Strickland案,为了表明审判不公,被告人必须证明辩护律师的错误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剥夺了他享有一个公正或可信赖的审判权,而不仅仅是审判结果不同。
(3)保障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制度——无效辩护制度
美国无效辩护制度是一项保障刑事被追诉人获得律师有效辩护和公正审判的制度。律师的失职行为侵害了被追诉人获得有效辩护的权利,此时需要无效辩护制度来承载救济被追诉人权利的功能。[27]
美国无效辩护制度包括以下内容:(1)无效辩护申请的提出。被初审法院定罪的被告人可以在上诉程序中提出无效辩护的申请,要求上诉法院裁判其在审判过程中获得的律师辩护是无效的,侵犯了被告人获得有效律师辩护的权利,无效辩护申请可以针对律师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不称职行为进行;(2)无效辩护申请的审查。由上诉法院根据相关的证据和判断标准对无效辩护申请进行审查;(3)无效辩护的后果。上诉法院认为存在无效辩护时,将撤销对被告人的定罪判决。[28]
(4)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案例及评析
在一切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享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众所周知,宪法保证刑事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获得律师的帮助,但如何界定律师的帮助是有效的呢?在1980年,政府以克罗尼克参与了13次邮件诈骗行为对其提出指控,并声称他在佛罗里达和俄克拉荷马州的银行间策划了一起复杂的支票造假计划。邮政的调查员花了近5年时间搜集了关于此案的大量证据文件。法院为克罗尼克指定了一名年轻的房地产律师,然而这个律师却从未代理过这类案件,并且法院仅仅给了这位律师25天的准备时间。而后克罗尼克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辩称法院为其指定的律师辩护行为构成律师无效帮助,侵害了宪法第六修正案赋予他的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据克罗尼克所述,“我的家庭自1949年9月19日就已经是美国家庭的一份子了。”克罗尼克本人是一个圆滑而又谦恭有礼的人,曾经还对他的处境发出过豪言壮语:“政府的宪法体系中的法律是权力的裁决者,像云一样总是看得见的,清晰流动,然而却坚不可摧。克罗尼克的诋毁者说他是一个极其圆滑的人,而他的支持者说他是一个正派的人,他的案子困扰着他也使他看起来多了一些傲慢。
在1973年,克罗尼克的父亲在佛州的坦帕市成立了Skyproof制造公司,主要经营对移动房屋的支撑捆绑业务。1974年,30岁的克罗尼克接管了这家公司。他雇佣了一个名叫卡罗琳·卡明斯的年轻妇女去做秘书工作。后来他任命卡明斯为公司的董事长,同时她也成为了公司的唯一的股东。克罗尼克交待说,他想要以匿名的方式保留这家新公司,因为此前经营的Skyproof制造公司破产了,使他声名狼藉,而且还被迫索赔。
1975年克罗尼克与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名诺曼银行职员梅里特结识了,梅里特让克罗尼克在银行为Skyproof公司开设一个账户。在6月到9月期间,每天都有数百张支票在佛州坦帕市的Skyproof银行与诺曼银行进行交易。克罗尼克处理每笔存款,但所有的支票及银行记录都签着女秘书梅里特的名字。后来政府宣称,支票交易是一个典型支票造假计划,在当时俄克拉荷马州是史无前例的。
在这起典型的支票造假计划中,造假者在A银行以记名的方式开了一个户头,他写了一个5信贷五万美元的巨额支票,然后又在B银行开了一个户头,存入来自A银行的五万美元支票,由于A银行的账户资金短缺而使支票不成立,但B银行未意识到这一事实,给造假者在B银行户头上即时信贷。七天之内,在A银行中的支票已经被收集,造假者在B银行的账户上写下了一张五万美元的支票,然后存到了在A银行的账户上,在那张支票存款之时,A银行给予了造假者即时信贷,并在信贷授权基础上,支付了之前那五万美元的支票。
事实上,造假者利用了时间差在不同的银行之间转移支票。计划中人为地平衡了银行账户,其实,造假者只是把这些无价值的纸张反复地变动了一下位置,又利用资金不足而遭到支票被拒付而抢占先机。在此期间,造假者可以使用人工膨胀的支票所得到的信用额度来申请免息贷款,最终达到使用空头支票诈骗目的。
1975年10月,支票交易开始后的四个月,Tampa银行的官员审核了Skyproof的账户,并断定这个公司是为使用空头支票进行诈骗活动的掩护者。Tampa银行立即退回Skyproof公司的支票,并且不再接收其他支票。当这些支票在诺曼银行被拒付而退回时,俄克拉荷马州银行官员传唤梅里特,并指控她实施了支票造假行为。
克罗尼克立即与诺曼银行的经理和律师取得联系。他说如果Skyproof账户有误,原因应该是记账人出错了。Skyproof公司发展迅速,而克罗尼克却说从未建立一个充分高效的结算系统,他向俄克拉荷马州的诺曼银行官员保证说,他从没有企图欺骗任何人,并且他保证如果账户上有任何透支,那他会处理好的。克罗尼克交给一封由Skyproof公司董事长卡明斯女士署名的信,以表明是她把所有可利用的资金转移到了诺曼银行。
次月,克罗尼克交给银行一张价值五十万元的期票,并且用Skyproof公司所有的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装瓶设备厂作为抵押。梅里特又一次在这些文件上签字。不到两周之后,在期票到期前,诺曼银行接管了装瓶设备厂,他们经营了两年,并无盈利和亏损。
这个银行也向美国邮政方面的督察员报告,假若俄克拉荷马州和佛罗里达州有诈骗犯的话,它也是通过美国邮政操作的,这就违反了联邦邮政诈骗法,邮政督察员和律师开始了跟踪两州之间数百张支票以及数千份文件的乏味工作。
四年半之后,1980年2月,格林办公室指控克罗尼克,梅里特,梅里特参与了13次邮件诈骗,指控他们在知道资金不足无法支付这些由Tampa银行开具的支票的情况下,以支票的形式存入俄克拉荷马州银行4,841,073.95美元。
梅里特和卡明斯愿意合作来面对此次指控。他们想证明自己只是这些诈骗实施活动的傀儡,克罗尼克才是幕后操纵者。梅里特想证实自己并无诈骗的意图,卡明斯也想证实自己曾经怀疑过这些奇怪的流动支票,但是克罗尼克告诉她这只是正常的交易,她只是从命行事罢了。而克罗尼克将要面临俄克拉荷马州联邦地区法院审判,且将科处65年监禁刑。
六月,克罗尼克聘请的律师同时又是梅里特的代理人,因属于利益冲突情形,故该律师撤出该案。当时克罗尼克告知法院自己聘请不起律师,请求法院为其指定一名律师为他提供帮助。当时在俄克拉荷马州联邦地区法院为贫困的被告人选择辩护律师是根据当地律师姓名的首字母在字母表上选择出来的,对于克罗尼克来说,俄克拉荷马州地区法院的尤邦克斯法官为其选择了名叫克瑞斯·克莱斯顿的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克莱斯顿是一位职业6年的房地产律师,但他从未代理过这类案件。他不精通程序和证据规则,还未在陪审团和法官面前进行交涉和辩论,他也不曾担心自己是否能够胜任此案。政府给了克莱斯顿律师一把存放有关克罗尼克案证据的储存室的钥匙,后来克莱斯顿说:“我当时看到这些案件记录,我完全震惊了,还感到有些害怕。”
根据克莱斯顿当时的陈述,他告诉尤邦克斯法官不能胜任代理这个案件,尤其是这种重罪案件。但法官说:“我相信你能做得很好。”克罗尼克对法官任命的律师也很担心,并且向法庭陈述了这一情况。尤邦克斯法官说:“如果你想自己选择律师,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已经拥有了律师。如果你想要自己的律师,那么你可以自己聘请。这名律师是在我们的选择系统下任命的……他有资格,要不然我也不会任命他。”尤邦克斯法官给了克莱斯顿律师25天的时间准备此案。
不论是骗子还是绅士,克罗尼克都不是消极被动的那个职员,他在各个方面都在为自己不懈地努力着——努力保持礼貌,保持乐观(他不论在多么坏的情况下,都不低落)并且不断地使自己的辩护更加完美。他在法庭和律师面前掩盖了自己当时的自我行动,他不断地催促克莱斯顿探寻装瓶厂的情况并对银行的记录进行重新审核。克罗尼克坚持说,他绝没有行骗,即使从最大程度上讲,也只是一些透支罢了,而且他已经还清了。克罗尼克在审判中呈递了许多票据,当时克罗尼克和克莱斯顿都在场,而却让克罗尼克的职员呆在隔间内。然而,在审判结束后,尤邦克斯法官告诉克罗尼克,他认为克莱斯顿已经做了不可思议的工作了。”克罗尼克对此表示赞同。
辩护方克莱斯顿不否认有行骗者的存在,也未否认诺曼银行损失了钱款。克莱斯顿的辩护词认为这一切都是卡明斯的错误,毕竟卡明斯女士是公司的董事长且是唯一的股东,另外她在每张票据及文件上的签了字,而克罗尼克的签名从未出现过。
是什么让克莱斯顿没有提出善意的辩护。在很多司法机关,包括俄克拉荷马州,只是呈递一些空头支票是不足以侵犯邮件诈骗法规来定罪的,个人必须要有欺诈的目的。克罗尼克之后的一名律师说:“如果我被支票拒付的话,而且我能很好的利用他,那说明我意图是正当的,无意诈骗。”来看克罗尼克这一方——他承诺自己正常利用了这些支票并且把资金和装瓶厂作为抵押转给了银行——如果陪审团一开始就认为克罗尼克蓄意诈骗的话,他们就不可能消除这一犯罪事实。另一方面,陪审团应当把这些行动看作是克罗尼克所称的“善意行为”其实是对自己邮件诈骗的一种完全辩护。
然而,克莱斯顿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法官也没有给陪审团人格有关于此“善意行为”辩护的任何指示。几项指控都是被亲眼证实的,克莱斯顿没有否认Skyproof的账户是一个骗局,诺曼银行官员证实他们银行的损失了四十到五十万美元。他们说虽然克罗尼克没有代表Skyproof公司签字,但是通过电话和一些会议,他们断定克罗尼克是有罪的,而卡明斯的立场是:“我只是按照克罗尼克说的来做的。”
克莱斯顿并未对此次辩护寻找目击证人或是其它证据,但是他反复强调克罗尼克并未参与此案的记录,如果真有人作案的话,那应归咎于卡明斯。
陪审团根据克罗尼克涉嫌参与13次案件中的11次来定罪,法官判其有期徒刑25年。
克莱斯顿尽职尽责地对上诉要求进行了备案,但是他的准备时间并不充分,克罗尼克随后被保释出狱,开始调查自己的案件,并准备上诉。在此期间,他找到了一个证据,那就是诺曼银行根本没有损失,因为他给予银行的装瓶厂的抵押额已足以偿还其透支额。另外,他发现根据宪法第六修正案的规定,他的律师的代理行为构成律师无效帮助。
起初,在英国,律师的权利是倒置的。如果一个人犯了叛国罪或刑事重罪,他是不被允许获得律师帮助的,但如果一个人涉嫌轻罪或被告人在民事诉讼中,他是可以拥有律师的全权帮助。此规定在英国人看来是无理的,于是遭到了攻击。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说:“如此不公正的学说,在我们这里是无法立足的。”美国最初的13个殖民地中12个都意识到了犯罪案件中律师的权利的重要性。
事实上,最高法院已经意识到,在所有权利之中,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远远比其他权利重要,因为这影响到被告在维护自己可能拥有的权利时所发挥的能力。”虽然,这些字眼在《权利法案》中并未出现,但宪法第六修正案提到了,它要求一个迅速获得公开的审判,一个公平的陪审团,从而确保公平的审判。修正案的前几条确保了个人进行控告犯罪的权利以及确保在面对强大的政府公权力时获得公平审判,而宪法第六修正案指出为被告人提供律师的帮助,从而是这种保证得以继续。
公平审判的基础建立是最高法院所提到的我们刑事司法系统中“唯一的力量”,这是一种对抗性程序。在美国宪法中,刑事审判是不容置疑的,在此过程中,由一个全能的法官和一个陪审团,他们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