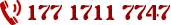法律随笔
李耀辉:律师怎么能为“坏人”辩护呢?
作者:李耀辉河北世纪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昨晚观看了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韩国影片《素媛》,我对素媛的不幸遭遇感到无比心痛,仿佛自己也跟着掉进了黑色深渊,虽然罪大恶极的坏人受到法律的审判,但他毫无悔意,法庭上律师以醉酒为由为其开脱罪责,弹幕上人神共愤,一片喊杀声,不明白律师为什么要替他辩护,法庭判决结果的荒谬不公,甚至作为刑辩律师的我都激愤到极点,换做是我肯定会拒绝为这种人辩护,但是总有人会站出来为他辩护,作为观众我们知道事件真相,假如真的冤枉了一个人,那对他及家庭的伤害可能不亚于对素媛的创伤,请客观理性看待律师为什么要替“坏人”辩护吧。
不论是在历史上的封建社会,还是当下的法治社会,辩护律师给人的印象,历来就是乘人之危,坑蒙拐骗,干扰司法,甚至唯利是图。普通大众对辩护律师进行嘲讽甚至打击报复,“铲除黑心律师”甚至废除律师制度的呼声不绝于耳。
在国外,律师也经常被当作嘲讽的对象,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人类最伟大的戏剧天才莎士比亚也发出过“杀光所有律师”的声音,亦有人将辩护律师运用法律手段维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的行为当成是“钻法律的空子”,还有人将辩护律师为那些被指控严重罪行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看作是为坏人开脱罪责,被误解为是“第二坏人”。刚刚剧终不久的《决胜法庭》抹黑律师,搞得整部剧唯有的两位律师可谓声名狼藉,职业形象也略显卑劣。
律师既不是正义的天使,也不是魔鬼的化身,律师首先是一个靠法律吃饭的人,律师为自己的当事人服务是他的职责所在,王人博教授说过:“我从不相信律师的神话,但我坚信好律师就是一个自己吃饱了还知道饥饿滋味的人。”
律师和教师两者之间是具有可比性,他们首先得赚钱养家糊口,两者不同在于,教师的人除了过日子还要育人,而律师则除了赚钱还得运送正义。纠纷造就了律师的兴盛,无知孕育了教师的壮大。
医师是人命关天的职业,法律职业何尝不是呢。他们的职业都关乎人命却并无二致,如果说医师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他的病人就算是“坏人”也需要竭尽全力予以救助的话,那么律师要为“坏人”辩护怎么就不具有职业正当性呢?美国著名的刑辩律师德肖微茨说:“即使我了解到有一天我为之辩护的委托人可能会再次出去杀人,我也不打算对帮助这些谋杀犯开脱罪责表示歉意,或感到内疚。……我知道我会为受害者感到难过,但我不希望我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就像一个医生治好一个病人,这个人后来杀了一个无辜的人是一样的道理。”
那种认为“律师为坏人辩护,所以律师也是“坏人”的观点,实际上是混淆了律师职业道德与一般社会道德的界限。律师的职业道德有时候会与社会道德发生冲突,但是从本质上看,两者之间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律师的职责正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田文昌律师曾举例言:“一个重要岗位的哨兵不能擅离职守,对眼前发生的其他事件去见义勇为,从表面上看,他似乎麻木不仁,违背社会道德,但是如若不然,却很可能由于顾此失彼而损害全社会的更高利益。”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那些受到国家刑事追诉的人被称为“罪犯”或者“犯人”,而刑诉法修改之后,被追诉人在审前程序被称为“犯罪嫌疑人”,在起诉之后被称为“被告人”,这样就不再使用“犯罪分子”这一称呼,其实这其中的变化不单是名称叫法上的变化,而正是我国刑诉法确立了不完整的无罪推定原则的体现。
无罪推定原则讲的就是未经法定程序确认有罪之前,应假定被告人无罪,这假定是一种法律拟制,并非主观认定。这种法律拟制是一种法律制度手段,在立法中多有运用,比如民法中的宣告死亡制度,我们假定被宣告人死亡,即使被害人重新出现,也不能据此认为宣告死亡制度本身错误。
我们假定被告人无罪,假设只是一个前提,还必须通过检察机关的举证和一套正当法律程序,通过法院的审理和宣判,才能最终确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反言之,假如我们不假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无罪,滥用权力,强迫自证其罪,剥夺其应有的权利,律师提供有害辩护,就像韩国电影《七号房的礼物》男主人公李九龙被冤死,令人感到悲伤,这样很容易冤枉好人,冤假错案也就很容易发生,这些年发生的冤案还少吗?
如果放纵一个坏人是犯了一个错,那么冤枉一个好人就是犯了两个错误,因为使一个好人受到了不应有的刑罚,还使得真正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据此我们肯定要两害相权取其轻,宁可放纵一个坏人,也不可冤枉一个好人,这样的价值取向也正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题中之义。
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言,法官只知道肯定的判断,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而从不说有疑问的判断,从不说案情不明。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在法庭宣判之前,是谁也说不清楚的,最后很可能会出现人们预想不到的“好人”有罪或者“坏人”无罪的结果。
既然被追诉人在法庭宣告其有罪之前,被当做无罪的人,那么他就理所当然的与公诉方在法庭上平等武装,享有其与未被追诉的人应有的宪法性权利,在刑事案件中,由具有专业知识和资格的律师为被告的公民进行辩护,是宪法赋予我国每个公民的权利,罗马法学家保罗曾说过:“辩护是使被告摆脱惩罚或减轻对其惩罚的条件。”
无罪推定尽管为被告人与国家公诉机关的平等理性对抗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但假如没有其他一系列的程序保障,被告人在与公诉机关的对抗中还将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而无法实施有效的防御。为确保控辩双方诉讼对抗的有效参与,各国法律几乎都确立了获得律师的帮助的程序保障。
可能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即使是犯罪分子也有其作为人而应当享有的尊严,也有其不应当受到剥夺的人权,侵犯人权的背后就是整个社会及其政府还没有学会尊重人权,还没有学会文明对待它犯错的公民。
一个人要是研究一下人类共同的基本需要,就会为人与人和谐相处和相互间的公平对待的观点找到一个立足点,例如,人都有生存的需要,我们自己想活,也要让别人活,当法律要剥夺我们自己的自由、生命和财产权利的时候,我们所需要得到公正审判和律师的帮助,那么别人也需要,而不管他们属于什么国家,哪一个阶级,什么政党,什么身份。
看一个国家是否文明有两个去处,一个是厕所,一个是监狱,现在我们的公厕经常提示我们,“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我们不能把监狱办得比社会还好,我们得到的就只能是比监狱还坏的社会。根据木桶原理的逻辑分析,把一个国家的文明和人权状况比作是一个木桶,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高低是由这个木桶最低的那个木板决定的,我们眼中的“坏人”就是最低那个板,如果充分保障“坏人”的基本人权,那么我们好人的权利也相应地提高了,也没有理由不会好的。所以,“坏人”是否得到尊重,是区分一个国家的文明与野蛮的一个标尺。
要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法网密布的社会中都有可能成为刑事被追诉的对象,如果你反驳说,我这一辈子遵纪守法总可以吧,那么你还记得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聂树斌吗?这些冤案的发生谁能说他们没有遵纪守法呢?影片《控方证人》中,当事人对律师说,没有人会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入狱的。律师中肯回答说我们只是努力不让这种事成为习惯。
人类文明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这巨大难题,就是如何保证无辜者不会蒙冤,有罪者罚当其罪?一个人自身遵纪守法很容易做到,但是你很难控制别人也遵纪守法或者嫁祸于你,甚至也不敢奢望具有威信力的司法机关遵纪守法,很多冤假错案也正是出自他们之手。回顾历史的教训,身受“文革”之苦的彭真同志在回顾“文革”遭遇时曾说过这样的意思:要有律师啊,他们不让我说话,总得有人替我说话吧。
根据古老的自然正义的要求,法官应该听取双方的陈述,这是衡量一项司法裁判程序是否公正的基本标准,而在刑事诉讼中,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于维护程序正义又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如果我们认同被告人需要法律的审判,从自然正义理念出发就可以寻找到法官必须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由于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的公诉机关,身后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作后盾,而被告人完全处于弱者的地位,如果不强化其辩护权,他只能是被拷问和追究的对象而不能成为诉讼主体,这与现代刑事诉讼机制的要求不相等。
为了能够与控方进行有效的对抗,法律的天平必须向被告方倾斜,理应认同杀被告人也需要专业的律师帮助,只有在律师的帮助下被告人才能起码的与控方平等对话,这是完全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和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