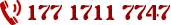平冤系列
刑案无论立案与否都已很难
诸多媒体8月12日报道了两个事件:一、在山东高密打工的安徽女子娜娜脖子被割断1/3死亡,卧室被翻并且失去钱财,警方认为系自杀不予立案,家属对此强烈质疑。二、贵州男子杨明坚持伸冤20年后被无罪释放,他系因1995年一宗奸杀案而判刑入狱。如果将这两个事件联系在一起看,也许能够对司法实践有所警示。
对于不了解详情的公众来说,可以不纠缠于两个事件的细节而进行各种经验假设。对山东高密事件,如果不假设为安徽女子非自杀,但不妨假设为或可能他杀、或可能自杀的存疑事件,因为毕竟警方承认该女子住所钱财失去的事实情节。进行这样的假设,也就是承认警方有理由不作为杀人案件立案,但也不承认警方将之作为自杀事件了结具有充分理由。奸杀案至少由于具备被奸的显然证据,因此对贵州男子杨明所涉1995年案件,可以假设警方不能作为自杀事件了结,而必须作为奸杀案件立案。
这样假设的意思是什么呢?贵州男子杨明所涉1995年案件为必须立案之奸杀案,但20年来已经被事实证明该案件并未被真正破获,然而20年前该案被立案之后,非作案人杨明被作为奸杀者被捕获并判决,体制性地破获了奸杀案。因此可以进一步认为该案系必须立案而必须破案所导致。山东高密事件尽管有明显的疑义,但当警方不掌握明确的杀人者证据情况下,从该案可以不立案的基础出发,采取排他思维作出不立案结论,从而就回避了必须破案的压力。总之,当对两个事件进行如上经验假设并推理后,就可以发现它们有其共同点:警方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立案困境,无论是冤案的造成还是排斥立案,都跟这一困境有直接的关联。
立案,就其本意而言,仅仅是警方就可能构成犯罪的事件作出进行侦查的程序手续。立案后,事件经侦查也许最终被确认为构成犯罪,也许最终不能被确认为构成犯罪,也即立案作为一个程序手续,并不能取代事实本身,不能意味着属于结论,它仅仅意味着警方对某种具有犯罪疑义的既有事实进一步探查真相的追求。简言之,警方的立案就是警方进行正式调查的启动程序,除此以外不具有更多的意义。也许,警方实际进行调查而并未立案,但立案一定意味着进行调查(侦查)。然而,在司法实践当中,这一点在中国一直是被扭曲的。由于调查缺乏对被调查者乃至相关人权利的尊重,不仅询问事实上具有强制色彩,而且更常见对于强制手段的滥用,调查本身已经意味着属于一种惩罚。因此,立案就发生了自我否定,它不再属于一种并不包含太多涵义的程序手续,而成为了一种十分严峻的处理属性的决定。
立案的这种自我否定所导致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就警方而言,立案成了自我束缚的枷锁,警方首先不是着眼于事件本身,而是更多考虑了自己的立场、能力和利益。就民众而言,立案与否成了评价警方立场的标准,并形成了进一步的可怕的进行事实推论的社会心理倾向,比如,一具死尸被发现,如果警方立案,社会心理就认定了其为被杀;一旦警方经调查后认定不属于他杀,社会心理就难以扭转,从而怀疑警方的侦查立场。相应地,就社会而言,民众就警方是否立案,形成了第一个矛盾焦点,不再是首先着眼于事件本身,而是着眼于或者要求警方立案,或者希望警方不予立案。
就体制本身而言,立案成为了对警方考绩的基本指标,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体制不是承认事件发生的数量事实,而是将警方立案数量取代了事实本身,形成了深刻的幻觉体系。进一步,以这幻觉体系为基础,引申出了凡立案就必须破获的刑事管理理念。由此又引起两个严重后果:一、凡可能破获不了的事件并可以抓到不立案理由的,警方职能部门就可能宁愿不予立案;二、凡已经立案的,可能即使冤枉他人也努力达到实现“破案”的目标。相应地,社会矛盾也由这两个方向延伸:对警方不立案的喊冤,以及对警方冤枉人的喊冤。
立案,这已经是一个深重的困局,无论警方还是民众,在根本角度都深受其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