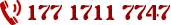法律随笔
李耀辉| 爱上刑事诉讼的五个理由
起初并不是我热爱刑事诉讼才选择它,而是选择了刑事诉讼才逐渐发现它有着其他部门法所不具有的独特魅力。作为律师专业化的选择一定需要自己热爱的那个专业学科的精神和理论支持。律师的专业化道路,必然需要精神与理论上的真正共鸣——而那正是刑事诉讼赋予我的力量。
回顾我的学习之路,大致可总结为三个阶段:起初通过学术随笔类书籍,培养程序思维与理念,建立兴趣;之后勤于思考与写作,结合真实案例提升分析能力;最后深入专业文献与经典著作,尝试完成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正是毕业论文的写作,让我明确了自己的人生志向:成为一名刑辩律师。
一、良师引路:超越名校的精神传承
2010年,我参加研究生考试,因一分之差与西北政法大学失之交臂,最终调剂至有“草原明珠”之称的内蒙古大学。我带着青春的炽热与理想走进内大法学院,师从法学院最具影响力的周宝峰教授,立志在学术道路上有所建树。
周老师的学术风格与人格魅力深深吸引了我。从我对刑诉的热忱,到最终走上刑辩律师之路,无不受到他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是周老师重塑了我的职业选择。
前不久,周老师对我说:“不为刑辩,不研刑辩,无以成大家。”刑辩之技,是律师的实战锋芒;刑辩之学,是律师的思想底蕴。李耀辉律师二者兼备,其“大律师”之誉,实至名归。
二、宪刑交融:刑事诉讼的宪法维度
刑事诉讼法与宪法具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以至于被一些学者形象地称为“国家基本法之测震器”、“应用之宪法”、“宪法之施行法”甚至“法治国的大宪章”。
就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来看,刑事诉讼法是依据宪法制定的,宪法权利通过刑事诉讼法进入司法程序并且形成其实现机制。宪法不仅决定着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而且还规范着刑事诉讼法的具体实施。在整个刑事诉讼领域中,国家权力的行使与公民权利的保障都必须由国家宪法予以直接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诉讼法上的权利是宪法权利的具体化,并且通过刑事诉讼法进入诉讼程序,是保障这些权利实现和有效行使的方法。
宪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大宪章,对于关系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对生命、自由、财产的限制甚至生杀予夺的刑事诉讼活动自然予以极大的关心。国家刑事诉讼程序的运行最容易使公民权利受到国家权力的严重侵犯,从而导致刑事诉讼领域成为人权保障最为迫切的国家权力行使区域,所以,刑事追诉与审判等国家权力行使活动必须受到宪法的决定和制约。
法学大师拉德布鲁赫在论及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性时曾精辟地指出:“如果将法律理解为社会生活的形式,那么作为“形式的法律”的程序法,则是这种形式的形式,它如同桅杆顶尖,对船身最轻微的运动也会作出强烈的摆动。”(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
三、程序优于实体:法治运行的内在逻辑
实体法与程序法,如车与轮:无车则轮无所承,无轮则车不能行。刑法界定罪与罚,刑诉法则规定如何认定罪、如何施行罚。
二者之间,我更推崇程序法的根本性地位。没有实体法,国家仍可施罚,却易陷于擅断;而程序法,恰恰是通过理性步骤约束公权、保障人权的制度设计。哪怕实体法严苛,只要程序公正,判决仍具可接受性。
因此,宁愿以完善的程序施行严苛的实体法,也不愿以暴戾的程序适用良善的实体法——唯有认识到这一点,才真正触摸到了法治的内核。
四、诉讼如战场:权力与权利的理性对抗
刑事诉讼,可谓国家与个人之间一场关于罪与罚的“战争”。它以控、辩、审三方为支点,构筑等边三角之构——法官居中裁判,控辩平等对抗。
这套制度设计,旨在通过规则与程序,实现权力制衡与权利保障。任何一方的强势,都将破坏诉讼的公正基础。唯有在程序中落实“平等武装”,才能保证对抗的理性与判决的权威。
五、刑辩之冠:律师事业的巅峰之境
刑事辩护,是律师业务皇冠上最亮的明珠,也是最富挑战、最显功力的领域。这是因为,刑事辩护关乎当事人的生与死,自由与囚禁、财产与隐私、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重罪与罪轻,与当事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牵动个人命运的最敏感神经。
与民事诉讼处理民间纠纷不同,刑辩直面的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对抗,涉及生命权、自由权等最基本人权。正是在这种高风险、高强度的辩护中,律师的价值与法治的精神,得以最深刻地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