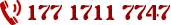法制新闻
吕良彪:司法改革的三大误区与成败关键
司法当有“定力”:既不能惯着权力,也不可迎合民众。“四下讨好”的司法不可能受到尊重。司法改革成败的核心,在于能否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国家需要“三驾马车”——立法权、行政权理应是拉着国家这驾马车积极前行的“主动型”权力;而相对消极、被动的司法权,则是驾驶着、约束着立法权、行政权不要脱离法治轨道的保障。我想,也是应该是“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带给我们的启示。
司法改革是当下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仅是法院的事,不仅仅是权力体系内部的事,而是所有法律人的事情,是全社会的事情。需要启蒙,需要普及常识,需要公布真相,需要社会博弈,需要社会共识,需要寻求我们的“最大公约数”。
——题记
第一个问题:当下司法改革的三大误区,或三个方向性错误
第一个误区:司法改革更多只是权力体系内部的“自娱自乐”
无疑,司法改革是当下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改革就是“变法”,几千年来莫不如此。——只是,那数千年的“法”都是权力工具之法,作为权力“治民之器”的法。历史表明:依靠权力体系内部的反腐败与政治体制改革注定都将走不出死胡同。——典型者如,中国为何会“越反越腐败”?因为权力者认为腐败是因为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监督,于是便设定一个更大的权力去管着那些可能腐败的官员。而更大的权力缺乏应有之监督,腐败的能力反而更强。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民众的有效参与,在于培育民主法治的土壤,需要司法的独立与媒体的自由。否则,建立在权力体系内部相互制约基础上的反腐败,无论声势如何浩大,说到底也不过是“守着粪堆打苍蝇”!——所以,当下的变“法”,当是公民权利保障之法,是监督制约权力之法。“没有民主法治制约权力,人人都行进在通往监狱的道路上;没有民主法治保护权利,任何财富的“神马”都不过是浮云。同样,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律师们不能科学、有效参与和监督的司法改革,都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律师无法阅卷、律师代理或辩护意见被无视,甚至连证据都被贪污、被曲解,而民众及其权利代言人的律师、记者、学者们根本没有一个法定的救济途径,“员额化”做得再精细也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改革。就如今天的论坛:前面各位讲得非常精彩但却“超时”,所以主持人就“本能地”责令我和王才亮律师发言时间从十五分钟减为十分钟——我想提请各位反思的是:关于发言时间,论坛有规则么?主持人有职责么?每位发言人有自律么?——没有这种坚定的法律人精神,每个人都自以为是地打着“擦边球”,司法改革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而且,每每出现社会问题的时候,治理措施便是限制公民权利:限行,限产,摇号......为什么?凭什么?
司法改革绝对不仅仅是法院、检察院的事情,绝对不仅仅党和政府等权力体系内部的事情,只有诸如学者、记者、律师及其所代表的民众能够充分参与,民众能够对权力享有充分的监督,中国的“全面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才可能有出路。当下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政治气候总体向“左”转、最高权力试图全面对社会加强管控的形势下,法律人的坚守至关重要。
第二个误区:司法缺乏“定力”地“四处讨好”,不可能赢得权威与尊重。
中国政治体系之下,司法一直处于权力的边缘。首席们也都按照各自不同的“四处讨好”的思路在试图改变着这种局面:
上个世纪末,我在一家中级法院担任审委会委员、研究室主任。当时法院正经历着一件大事:换装。我们摘下了头顶上的大盖帽,脱下了戴肩章的制服,穿上了西服和法袍。——当时,最高法院院长是肖扬。他所主导的司法改革,我总结为“师爷化”的路子:也就是试图以强调司法的独立性、中立性与权威性改变司法在权力格局中的边缘化状态。——大家知道,穿“制服”者的特点是上级管理与下级服从,而穿西服着法袍则意味着专业、独立、中立,甚至某种神秘化。
十年后,司法改革进入王胜俊乃至“周永康”时代,以“维稳”为特色的司法呈现出某种“伙计化”的路子:即试图通过强化司法的工具性职能讨好权力来强化自己的权力格局中的地位,强调“调解率”、强调根据人民群众的感受和评价判案、强调“三个至上”。——公安、检察干不了的很多事情,只有我法院才能(为领导)干成。在这种大的背景与思路下,司法日渐沉沦与“家丁化”也就成为必然。
现任的周强院长因其专业背景与政界阅历而广受关注与期待。十八届四中全会则全面描绘了司法改革的三个基本方向:
一是司法“去地方化”,例如由省级法院统一管理全省法院的人、财、物——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统一管理”绝不等同于“垂直管理”,因为上下级法院之间绝非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又如,跨行政地域设立高级法院,设立南北巡回法庭,等等。
二是司法“去行政化”,在法院内部主要是解决好审者能判、判者必须审的问题,解决好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与工作方式问题,例如北京知产法院审委会全体委员同案听审,解决好院庭长与审判人员之间的责权利关系问题。
三是司法“去暗箱化”,比如强调审判公开,裁判文书上网等等,试图以公开化促进司法公正。
以上司法改革大方向无疑是不错的,但囿于当下宏观权力结构限制,周氏司法改革无力将司法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后山小路”或“正面阵地”,而选择以“苦练内功”为特色的“法官员额化”为着力点,而法庭审理、司法文书羞答答的所谓公开又实现不了司法的民主化,难免陷入双重尴尬。值得期待的是:“法官员额化”的改革,或许可能打造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精英化”的法官队伍。
常识在于:“越讨好越没地位”。李天一案的重判,无非司法在迎合民粹;夏俊峰案的判死,相当意义上是司法在迎合权力。
我在武汉仲裁委裁案子时,曾有其他仲裁员老师担忧:吕老师,这样裁政府能接受吗?政府不接受仲裁裁决还能执行吗?如果政府不执行这案子是不是裁得就会有问题?——我当时说,如果裁判不是依据法律和事实,而是考虑被裁判者的感受,那裁决还有何权威公正可言呢?!仲裁裁决不仅仅要考虑执行的困难程度,也要考虑对正义的宣示程度。——此案裁决后,政府虽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尊重并执行。
我在北京仲裁委曾经仲裁过一起当事人上访十多年的案子:河南农民在湖北承包的百余亩林地,在修建高速公路时被政府强行处置造成损失,但政府始终不肯给予足够补偿。当事人为此上访十余年,后基于对法院公权力的不信任,最终选择到北仲仲裁,并由北仲指定所有仲裁员。此案仲裁庭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裁决,政府纵有千般不情愿,最终还是依照裁决给予当事人补偿。这种中立与权威,最终促成了社会矛盾的解决。
以上两起案件,是想说明:国家需要“三驾马车”——立法权、行政权理应是拉着国家这驾马车积极前行的“主动型”权力;而相对消极、被动的司法权,则是驾驶着、约束着立法权、行政权不要脱离法治轨道的保障。我想,也是应该是“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带给我们的启示。
第三个误区:司法权向“低处”将就。
院庭长、审判委员委员们不办案,行使司法权的法官层级越整越低注定是个方向性错误。
中国人自古讲究“老爷升堂问案”,司法断案权由一地最高长官掌管,具备最高的权威。即使随着官僚制度的细化,司法权、断案者依然具备相当高的职位与权威。民国时期的法官(推事)虽然按照专业分工产生,但其在整个社会中的公信力与权威度亦是不容否认的。“新中国”成立后,“推事推事,一推了事”怎么行呢?“法官法官,高高在上”怎么可以呢?所以法官推事被“人民审判员”化,从“高高在上”到走入“田间地头”,司法的独立与权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下司法改革,如果还是将具体审判权从院庭长往下移,是不是会进一步“矮化”司法权呢?!——的确,司法的权威并不完全来自级别。但官本位之下,往往没有足够级别便没有相应权威。我始终主张:基层法院法官级别不应副处级;中级法院法官,级别不应低于正处级;高级法院法官,级别不应低于副厅级;最高法院法官,级别不应低于正局级。
所以,我始终主张:一个法院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法官。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们,理应是业务骨干,才应该是办案的主力军。我一直设想由这些资深精英法官行使裁判权,其他现有法官及工作人员可以担任法官助理或助理法官,可以在这些法官的指挥下做好裁判辅助性工作。——所谓“案多人少”其实相当程度上是个伪命题:中国法官在中国人口数中所占的比例要高于美国;案件多主要集中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中心城市;即使案件多,也是可以通过改善法院审判机制去解决的。
法官精英化、相对稀缺化以后,法官员额制、法官高薪制、法官尊贵化等,都不是问题。
第二个问题:司法改革成败的核心在于能否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曾经,北大贺卫方教授与法大何兵教授这样两位语言大师级的法学家讲过一段精彩的“对口相声”,主题是司法应该精英化还是应当民主化,甚是热闹。
在我看来,司法的精英化与民主化原本就是尊重司法规律之下的“一体两面”:
毫无疑问:司法必须精英化,最核心的就是法官精英化。——对此,各界似已有共识。
毋庸置疑:司法必须民主化,即司法过程必须阳光,必须受到应有的、符合司法规律的监督与制约。
司法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相同的政治伦理与运行逻辑。现代国家,人们已经认识到:全民直接参与的往往会使民主沦为民粹。所以,代议制已成为各种民主政体的共同选择。——司法亦是如此:司法的过程不应是当事人可以任性民主表达的过程,而应当是律师作为当事人权利代言人与代理人,如何有效参与司法审判过程,有效监督制约司法权力运行,有效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的过程。——所以,司法改革成败的基础绝对不是权力体系内部的“自娱自乐”,而是能够保障作为公民权利代理人的律师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而是使媒体这一公众的耳目与喉舌能够符合司法规律地进行监督制约。
第三个问题:司法改革需要“法律人的理性与精神”
前面我已经讲到过论坛中所体现的法律人精神:规则;执法;自律。接下来,我想就律师的职业精神讲几句话:
“锋锐事件”后,“死磕”似乎成了一个律师胡闹的贬义词,这是不妥当的。象今天在台上的田文昌律师、王才亮律师,都是具有“死磕”精神、具有法律人精神的律师。例如面对天津公安的违法乱作为,田文昌律师就公开向最高检举报并通过媒体广泛发布。——这种以特别的方式,通过媒体、自媒体发布,从而吸引社会舆论广泛关注,最终迫使任性的权力不得不讲道理的过程,不就是标准的“死磕”么?!所谓“死磕”,核心意义上无非是律师争一个“讲理的法庭”、“说理的平台”。——所以,不要污名化律师的抗争,不要污名化抗争中的律师。
同时,我也想对律师同行说一句:死磕既要有骨头,还要有头脑;既要有好的出发点,也要有一个合适的度的掌握。某些律师消费行业整体利益进行的得瑟式营销,是我所反对的。
田文昌律师曾经说: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
我认为:作为“在野法曹”,律师是国家赋予公民免受政府伤害的“自卫之剑”;作为“专业人士”,律师是全社会的“法律雇佣军”。
田文昌律师曾经说:律师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
我认为:律师当心向正义而不以正义自居。——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受到错误的刑事追究而成为公众眼中的“坏人”,所以律师注定要“为坏人说好话”,为“邪恶”辩护,为“异端”张目。——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就是律师最大的正义。当下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深刻变革的复杂时代:杨佳式的社会报复以及天津、柳州大爆炸乃至新疆暴恐都在相当意义上警示着司法救济与社会治理的失灵。——以牺牲“维权”的方式进行的“维稳”还能持续多久?“上有西太后、下有义和团”的社会状态如何改变?社会是温和改良式的前行,还是辛亥革命式的剧变?当此社会深刻变革的伟大历史时期,法律人的理性、良知与责任,就是要在权力无度与民粹暴戾之间,构建起理性的防火墙。